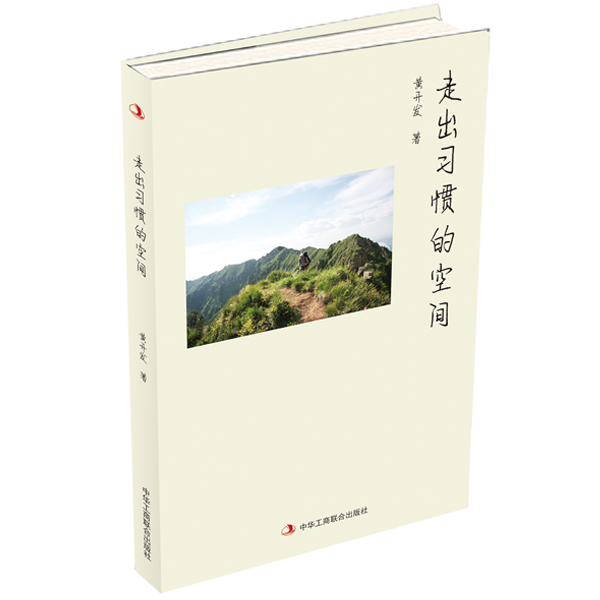走出习惯的空间
时间:2016/4/12 0:00:00
旅行的意义(代序)
经常在各种媒介上看到“旅行的意义” 之类的题目,题目很大。 每个旅行者都有自己的目的, 每次旅行的动机都会有所不同, 要想做出几条本质性的概括来, 实在很难。 也许, 向往远方是人与生俱来的趋向。
记得十来岁时, 我倚门而望, 远处天际线上大别山峰峦叠嶂。 大山那边是什么地方呢? 我问。 大人答, 那边是平阳。 “平阳”大约是平地的意思, 我猜。 平阳那边又是什么呢? 大人支吾起来。 第一次旅行是上初中的时候, 用过年参与大人赌博赢来的钱, 与小叔一起专程前往离家50余里的金寨县城——梅山镇, 看传说中的梅山水库大坝。 也不知道大坝让不让靠近, 我俩硬着头皮往库区大门里面走, 结果被门卫喝住。 然后逛镇子里的新华书店, 看见一本叫《 红岩》的书, 看样子像是自己感兴趣的写打仗的书, 于是买下。拿到手后翻阅, 发现其中有“中美合作所” 字样, 感到很陌生, 不像是自己的菜, 赶紧又退掉了。 可以说, 这是一次失败的旅行。
1982年上大学, 第一次进入城市。 连买饭菜票的钱都成问题, 自然没有闲钱出去游山玩水。 硕士毕业后工作,工资很少, 也无法支持长途的旅行。 一直到2000年博士毕业, 收入的情况才有所好转, 旅行的热情开始高涨起来,而且脚步一迈开, 便收不住。 出国旅行始自2002年, 那一年去汉城( 当时的中文名字还没有改为首尔) 的一所大学任教。 2013—2015年间, 又旅居丹麦。 从2002—2015年的十三年间, 去过中国所有的边疆省份, 寻访了不少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; 遍游韩国, 北起“三八线” , 南到济州岛; 走过了欧洲近二十个国家和地区, 南到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西亚, 东至白俄罗斯, 西抵苏格兰的斯凯岛, 北及挪威北端、 冰岛, 还去了北极圈内地属北美洲的格陵兰。 回顾十几年的旅行经历, 翻看积累下来的旅行记, 感觉对“ 旅行” 的意义有了一些自己的体会。
旅行就是走出习惯的空间, 到另一个地方去。 其中包括办事、 游览和朝圣。 这里所谈的“旅行” 主要指的是游览, 办事的情况要复杂得多, 朝圣又很特殊。 对旅行者来说, 旅行是一种爱好。 王国维曾以叔本华的哲学来解释人生和艺术, 在《 红楼梦评论》 中有对叔本华哲学思想的集中表述: 生活的本质就是欲望, 这是人的生活意志的表现。 有欲望则求满足, 然而欲壑难填, 人得不到最终的慰藉。 即使欲望得到了满足, 厌倦之情又会乘之而起。 所以, 人生就像钟摆一样, 往复于痛苦与厌倦之间, 而厌倦又可视为苦痛的一种。 王氏在《 人类嗜好之研究》 《 去毒篇》 中说, 人因为有空虚的苦痛, 所以需要慰藉, 于是就有了各种嗜好。 嗜好有高尚、 卑劣之分, 这就需要通过教育来培养高尚的嗜好和趣味。 人间的爱好五花八门, 什么人玩什么鸟, 吃喝嫖赌抽都可以是爱好。 然而, 爱好有有益与有害之别。 这里除了社会上公认的标准外, 还有对个人的适宜问题。 比如我平时做案头工作, 不喜欢在业余时间里再坐下来搓麻将、 打扑克或下围棋; 喜欢安静, 不愿去酒吧、 舞厅或其他热闹的地方。
旅行作为一种爱好, 虽然谈不上什么高尚不高尚, 然而健康、 有益。 旅行就像一辆车, 上面是可以装载很多不同东西的。 有一句众所周知的古训: 读万卷书, 行万里路。 后四个字主要强调的是旅行的认识作用。 陆游诗云:“ 纸上得来终觉浅, 绝知此事要躬行。 ” 书本知识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, 所以要与实践相结合。 旅行作为实践的一种, 可以突破书斋的局限, 到外面的世界去见识更广泛的自然、 社会和人生, 深化、 扩充或修正自己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。
人在旅途, 周围的事物对自己不构成利害关系, 旅行者摆脱了生存之欲的束缚, 心灵获得自由, 于是可以静观万物, 感受精神的愉悦。 中外艺术家早已发现自然可以给人以启示, 对心灵具有净化、 抚慰、 复原的作用, 并留下了大量的杰作。 就我自己来看, 每当驾车离开城市, 扑入大自然的怀抱, 都感觉世界顿时安静下来, 身体好像启动了另外一套程序。 行走在山水之中, 清风拂面, 风景洗目, 被城市生活消磨掉的元气开始恢复。 这时候, 心灵变得特别柔软、 易感, 不自觉地调整到与环境合拍的状态。 遇到一片蓬勃的野花,会柔情满怀; 面对高山大河, 则又是气壮神旺。
记得在云南梅里雪山徒步, 头顶上是雪山, 身边是深切的世界级大峡谷, 似乎感觉得到血管里血液的奔流。 犹如刘勰在《 文心雕龙》 中所说:“ 登山则情满于山, 观海则意溢于海。 ”一个人与大自然接触多了, 潜移默化会形成一种山水情怀。 由于心中有丘壑、 烟霞, 哪怕生活在人欲横流的闹市中, 也能获得内心的清净, 不易迷失自我。 其实不仅置身于大自然, 就是在异乡的村庄、 小镇甚至都市中, 旅行者也摆脱了与周围环境的利害关系, 换一种眼光看世界。 这时候, 没有人跟你谈生意经, 你会发现周围的人变了, 变得更有风致, 更可爱; 你也变了, 变得更通情理, 更好奇、 爱思考。 总之, 他乡成了令人流连的风景。 旅途中也难免碰到不愉快的事情, 但因为旅行者与环境不具有固定的关系, 是一次性的, 所以不会带来长期的困扰。 十几年来, 我得以时常从原有的栖身之所走出来,见识了不同地区的人生百态, 动摇了从小被灌输的成功观念, 发现人生更多的可能性, 从而减少了“我执” 。 我自认为是一个原始自然景观的爱好者, 或者更准确地说, 喜爱原始自然风光与特定环境下人文的结合。
翻阅过去的旅行记, 写都市的少, 写乡野的多; 即便是写都市的, 也侧重于记述都市中闲暇的一面。 跑过不少偏远、 较少现代文明波及的地方, 看到了一些较为极端环境下的生存。 2004年7—8月间, 我和妻子新婚旅行, 走进过藏北高寒草原上藏民的毡房。 里面空空如也, 只有简单的生活用具, 脏兮兮的铺盖卷, 中间的炉子里燃烧着牛粪饼。 牧民们不会说汉语, 他们用质朴、 温暖的笑容欢迎着不速之客。 他们都是真正有信仰的人, 会在某个时间里摩顶放踵地去朝圣。在巴丹吉林沙漠的腹地, 沙白色土屋的嘎查( 村子) 几乎与环境融为一体, 一年四季风沙肆虐, 酷热酷冷, 人们靠放牧和挖草药顽强地生存。 从这些边民身上, 我深感生活其实可以很简单, 我们所追骛的很多东西与人生幸福并没有多大关系。 有一些旅行者, 他们喜欢一个地方, 于是停下了云游的脚步, 自己开起了客栈。 在迪庆的香格里拉,在梅里雪山下的飞来寺, 在内蒙古东部边陲的阿尔山, 我们都遇到过这样的人。 另据媒体报道, 2006年, 在虎跳峡的中虎跳, 一个工作于上海的日本女博士爱上了那里的山水和人, 嫁给了当地农民, 办起了客栈。 现在, 我又旅居北欧, 领略着西方发达国家的众生相。 参照千姿百态的生活方式, 发觉自己在都市里的那“一亩三分地” 真的没那么重要, 那么值得炫耀; 自我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, 不必太在意一时的荣辱得失。
在这个视觉文化盛行的时代, 人们习惯于不好好说话, 喜欢戏剧化的表演, 有着太多名利的计较, 缺乏土气和真气。 我一次次远行, 前往那些山高皇帝远的地区,寻找着、 领略着、 学习着那种简单、 质朴、 率真的表达方式。 我喜欢那些边缘人温暖的笑容, 爱听他们亲切的话语, 欣赏他们表达自己喜怒哀乐的简单方式。 在梅里雪山深处上雨崩村的晚上, 我们与几个村民围着屋内的火塘跳弦子舞。 在贵州黎平侗寨的风雨楼下, 与当地人一样交份子钱, 与他们一起享用长桌婚宴, 边喝着自家酿造的米酒, 边笑谈彼此关心的话题。 在雪域高原, 有几次偶然的机会, 听到藏族女子即兴的演唱, 那嘹亮的歌声如同蓝天圣湖般纯净。 西双版纳橄榄坝每天都要表演泼水节,看到花蝴蝶般彩装的姑娘们表情木然地跳舞, 兴味索然。然而, 在黄昏时分, 我们来到澜沧江边看落日。 夕照中,一个穿着筒裙、 身姿婀娜的年轻女子挑着小水桶, 从身旁款款走过。 附近的一支芦笙吹响, 旋律简单而优美, 流露出怡然自得之态, 感觉那乐声与土地是那么亲近, 如同天籁。 这些美好的时刻永远珍藏在了记忆里, 成为在都市滚滚红尘中保持内心清静的精神资源。
谭盾作品《 九歌》 里的音乐完全是用陶乐器演奏的,他曾自报家门:“ 这组音乐表达了我决意在非常嘈杂的社会中, 寻找一片安详宁静的故乡; 在嘈杂、 现代、 奢侈和尘世中间, 寻找一种朴实、 粗犷、 人类本能的、 爱的表达方式。 ” 这话深得我心, 自己在旅行中所要寻找的不正是这些吗? 谭盾的追求在音乐中得到象征性的实现, 我虽然步入了真实的山水, 然而很难说不是一种象征性的满足。 到达旅行目的地后, 看什么与不看什么, 强调什么与忽视什么, 是有选择性的。 好多被津津乐道的东西其实只是游客的想象。 不过, 这也是有积极意义的, 可以让游客与观看对象之间保持适当的审美距离。 很多时候, 真实的存在是不美的。
2015年5月27日